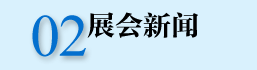【作 者】曾晓红:上海古籍出版社
【摘 要】“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经典出版工程之一,其主体部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先后被列为“2011—2020年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分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文章回顾了“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项目实施的来龙去脉,梳理总结打造这项文化出版精品工程的顶层设计、出版历程、编辑经验及重大意义,全面呈现几代藏学专家、出版人的筚路蓝缕之功。
【关键词】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英、法、甘藏敦煌藏文文献;精品文化工程;民族文献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
“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持续十多年的经典出版工程之一,先后被列为“2011—2020年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分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其主体部分《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1]总规模为35册,已经出版23册,计划2020年底结项;《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2]总规模为25册,已经出版9册,计划2020年结项;《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3]总规模为30册,已经出版18册,计划2019年底结项。自2004年项目运行以来,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出版作为一项重大原创性精品文化工程,集几代藏学专家、出版人的筚路蓝缕之功。对这项工程的重大意义,学界评价甚高。2006年《法藏敦煌藏文文献》陆续出版后,藏学泰斗、中央民族大学王尧教授曾说,对这项成果“怎么估计都不会过高”。日本著名敦煌学家、藏学家今枝由郎则说,“这对于藏学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国内藏学领军人物沈卫荣先生认为,“引领中国藏学研究真正能与国际学术接轨,并走向世界前列,《法藏敦煌藏文文献》《英藏敦煌藏文文献》等基础类的第一手文献的整理刊布更是重中之重,其出版惠及学界,功在千秋。”笔者作为“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的项目参与者,回首十余年来的出版之路,既欣喜于成绩的取得,也感慨于出版过程的艰辛。
一、历史使命:海外古藏文文献出版回归
明清档案、甲骨文、敦煌吐鲁番遗书、居延汉简被称为近代古文献的四大发现。敦煌藏经洞出土了公元5—11世纪的佛教经卷、社会文书、刺绣、绢画、法器等文物5万余件,为研究中国及中亚古代历史提供了数量极其巨大、内容极为丰富的珍贵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其中包括2万余件敦煌古藏文文献。
敦煌遗书之流散,当追溯到1900年王道士偶然间打开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从此,包括敦煌古藏文文献在内的敦煌遗书经历了离奇曲折的命运,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奥登堡、美国的华尔纳、日本的橘瑞超……各国“探险家”们纷至沓来,国之重宝纷纷被盗掘、骗购,几经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乃至世界各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七八十年代,敦煌古藏文文献成为国际藏学研究最前沿的阵地,基本反映了国际藏学研究最高学术水平。然而,由于英国斯坦因、法国伯希和所获的敦煌、新疆古藏文文献约10 000件,几乎占文献总数“半壁江山”,这些文献都深藏在伦敦和巴黎,中国学者很难利用。中国最杰出、最优秀的藏学家,疲于奔命往返于各收藏机构,期待一睹文献真容。即便时至今日,中国藏学家对敦煌古藏文文献的研究也往往落于人后,对吐蕃佛教的研究也不尽人意。二十一世纪,敦煌学已经成为国际显学,经过近百年来的奋勇追赶,我国敦煌学人在国际敦煌学界已可发出有说服力的“中国的声音”,但敦煌藏文文献的研究仍是较为薄弱的领域,甚至有学者坦言,国内敦煌藏文文献研究的滞后,一定程度上拖了整个“敦煌学”的后腿。
敦煌古藏文文献作为解读吐蕃历史文化最权威的文献资料,被称为破解吐蕃历史之谜的一把钥匙。西藏历史以公元848—851年吐蕃王朝的灭亡为界,分为“前弘期”和“后弘期”。敦煌藏经洞发现的2万余件藏文文献全部是“前弘期”的,其价值难以估量。作为已知现存的最古老的纸质藏文文献,这批文献种类有佛教经典、历史著作、契约文书、政事文书、法律条文、占卜、传说故事、苯教仪轨、文学著作、翻译著作、书信等,涉及吐蕃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文字等诸多方面,不仅是研究吐蕃历史、文化、宗教等的第一手珍贵史料,也是中古时期汉藏文化交流的重要见证。
敦煌藏文文献也是丝绸之路文明研究的必备文献。公元七世纪下半叶开始,吐蕃王朝发动对周边的扩张战争,占领了唐朝以及西域各国的大片领土,当时地处中西交通要道上的敦煌也在吐蕃管辖和治理的范围之内,并处于吐蕃统治区的地理中心,吐蕃王朝代替唐朝担负起保护和管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通道——丝绸之路的任务。赞普的王妃和宰相在敦煌组织和主持了佛经的翻译、抄写和传播事业。在吐蕃统治敦煌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吐蕃语成为陇右乃至中亚的通用语言。这批文献对于研究丝绸之路沿线中亚文明的交流和融合具有无可替代、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4]
大批敦煌文献流失海外是几代学人的锥心之痛,面对文物尚无力回归的现实,面对学术界、出版界在敦煌古藏文基础性文献资料方面的巨大空白,面对国内藏学研究举步维艰、难以同国际同行比肩的学术困境,几代学人殷切期待着海外敦煌古藏文文献先期整理刊布。
在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感召下,上海古籍出版社历任领导以极大的魄力始终坚持专业学术出版定位,于2004年,克服重重困难,在敦煌文献汉文部分先期影印出版的契机下,将敦煌古藏文文献等海外民族文献的出版回归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多方的协助和努力下,“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应运而生。
二、多方护航:打造文化出版精品工程
“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的子工程和延续项目。1989年,“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正式立项,全社上下高度重视,以打造精品工程为目标,由社长、总编亲自领队,组建以编辑室主任、编辑、摄影、美编为核心的出版团队,分赴俄、法、英各国收藏机构,共派出工作小组10余批。在经费极度压缩的艰难条件下,海外工作团队通过现场拍摄、分工著录,有计划、有步骤地将分藏各国的文献、文物影印出版。这批文献的出版,极大便利了学界对敦煌文献的利用,同时也符合国家战略——让散失在海外的文献、文物以各种形式返回祖国。此举不仅开风气之先,更满足了学界需求,引领着该学科的发展。[5]
“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立项之初,上海古籍出版社领导就着手从顶层设计推动民族文献出版形成规模效应,制定了先出版汉文部分再出版民族文献部分的设想。200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列为出版社重大项目,与西北民族大学合作,联络英国、法国国家图书馆,准备整理出版流失海外的敦煌民族古文献,“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获得了各文献收藏机构的大力支持。2005年4月,在国际敦煌项目(IDP)第六次会议(北京)期间,出版方和英、法两国图书馆负责人商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分别签署了合作编纂出版的意向书及实施细则。[6]随即,出版社在组织领导、人员调配、出版保障等各方面对项目实际运行给予大力支持,由总编亲自挂帅,抽调业务骨干,整合了一支精干的编、印、发团队。
“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自立项开始就以“打造学术精品”为目标,从开本选择,到内容编排,再到印制工艺,不断与时俱进,走专业化、国际化出版路线。开本选择时,以“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项目为参照,采用8开大开本。英藏、法藏藏文文献图版部分,根据当时的条件,正文采用黑白图片编排,遴选重要的写卷作为彩色插页,二者形成互补,既可使研究者对文书写卷内容有清晰认识,又可通过彩色插图还原写卷原本形态,帮助研究者大体把握文献的文物性。至2017年底《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之际,由于技术条件的成熟,采用了全彩印刷,最大可能保持写本原貌,方便学者对文献进行全方位考察。编排图片时,一般不超过写本的原始尺寸,部分文献或因物理特性或因漫漶残损,适当放大或缩印,对图片进行细节处理,以帮助研究者研读文献内容。“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的英藏、法藏部分,因合作编纂方中包括法国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国家图书馆,文献编订过程充分考虑到了国际性,定名采用藏——汉双语,并根据出版合作方的不同,序言、前言、前后附件等则采用了中、藏、英、法等结合的多语言呈现形式。
在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过程中,英藏、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编纂方西北民族大学成立了海外民族文献研究所专司其事,组织藏学、史学、文献学等各方面的专家,对海外敦煌藏文文献进行编辑、整理、研究,编辑工作精益求精、考订工作慎之又慎。西北民族大学地处金城兰州,在藏学研究及民族文献整理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并有丰厚的学术积淀和丰硕的研究成果,拥有多识、华侃、才让、扎西当知、嘎藏陀美等一批著名的藏学和文献学方面的研究专家。研究所汇集了相关领域最优秀的学者力量,对海外藏民族文献开展广泛调查,核实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收藏、出版情况。编撰团队成员与出版社编辑组队多次赴各收藏机构,对史料进行调查和研读。“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启动后,购买了各收藏机构的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完整的缩微胶片。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兴起,研究所也与时俱进,充分利用西北民族大学信息研究院“国家民委藏文信息技术重点实验室”和“藏语言文化学院网络实验室”进行该项目的科研,将传统的文献学与现代计算机技术相结合,综合藏学、文献学、考古学、语言学、计算机技术等学科,充分发挥数码技术等现代高科技的优势,在较短时间里保质保量完成了文献及吐蕃早期语言文字的整理研究工作。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为将该项目打造成文化出版精品工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是英藏、法藏敦煌藏文文献之外的又一大宗收藏,其出版列入“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该图录由甘肃省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研究员马德、勘措吉主编,编纂团队联合兰州大学、西北民族大学等藏学、历史学、文献学专家,在《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叙录》的基础之上进行整理。近年来,数字摄影、摄像技术突飞猛进,国际敦煌项目“IDP”采用高清复原技术,公布了一大批写本文献的彩色照片。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在《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出版中及时更新技术,该项目拟出版甘肃13家收藏单位收藏的6672件敦煌藏文文献,所有近万幅文书的拍摄均采用高清数字拍摄,全彩印制,数码印刷。新技术的运用既节约了成本,也提高了图版清晰度,方便学者对写卷外观有更直观的认识,极大便利了学术研究和利用。[7]
“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对“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唱响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旋律,引导各族人民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认同,引导各族群众凝心聚力奔小康,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携手奋进新时代”具有重要意义。承载着民族团结的深厚嘱托,汇聚着几代藏学专家、出版人的精诚智慧,倾注着各级领导的关怀与期望,“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扬帆起航。
三、精益求精:匠心独运保障专业水准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学者型编辑”辈出的年代,其时适逢敦煌学在国内蓬勃发展,预流此学术潮流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敦煌吐鲁番文献集成”“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等项目培养人才,编辑从做中学,从学中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贯穿于出版工作的全过程,涌现出一批学者型编辑。
编辑自身的学养不足,则判断不出所编辑图书的学术质量的高下,提不出高水准的修改意见。为了与作者沟通对话,真正做到服务作者、服务学术,“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的编辑在工作中发扬工匠精神,学会用“两条腿走路”:一方面,加强职业素养,从修正书稿的错别字、标点符号等硬伤做起,对书稿的学术科学性、文字规范性、表达严谨性、知识准确性、逻辑思维缜密性等多方面把关,同时练好内功,做到编、印、发心中一盘棋,全面把控装帧设计、印刷工艺、纸张用料等细节;另一方面,提高学术水平,时刻关注研究领域的学术进展,从梳理学术史开始,研读能找到的全部参考资料,做到既拿得起红笔改稿子,更拿得起蓝笔写稿子,争取成为“学者型编辑”。[8]
古籍出版专业的编辑,不懂藏文是先天缺憾。正如傅斯年所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尽力通过学习佛教学、学习藏传佛教的历史和文献学来弥补。如《大正藏》密教部分,王尧、陈践先生的《吐蕃历史文书》《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藏文文献解题目录》等,都是我们经常翻阅的案头必备书。西藏史学部分,如《青史》《红史》《西藏简史》《吐蕃僧诤记》《吐蕃年表》《吐蕃编年史》等名著,对我们了解西藏早期历史及藏传佛教早期发展的历史大有裨益。为了弥补编辑人员不懂藏文的不足,为了更好地服务作者、把好质量关,我们自行摸索出一套虽不科学、不完备,但往往行之有效的编校方法。这套方法主要得益于著名佛学专家周叔迦先生编制西夏文文献目录的启发。周先生当年不认识西夏字,但硬是帮助北京图书馆编制了馆藏西夏文文献的目录。据周先生自述,他的方法就是比对字数。他可以根据某标题确定是《华严经》,根据某章节的字数确定是《华严经》的某一章节。周先生的方法给予我们很大的鼓舞,我们通过向西北民族大学专家请教一些藏语的基本语法,熟悉藏文文献定名的词汇、句式和习惯,通过音节、字数的比较,经常从音节、符号、书写格式等方面提出疑问,果然能据此发现一些疏漏,帮助编纂者纠正了一些错误、缺陷。
为了在编辑环节中对写本的定名更有把握,编辑一方面对《敦煌研究》《敦煌学辑刊》《中国藏学》《西域研究》《敦煌吐鲁番研究》等专业学术刊物发表的敦煌藏文文献研究论文、著作时刻留心,尽可能搜集资料,关注学术进展;另一方面广泛搜集中外整理的敦煌藏文目录、论著进行比照对勘。
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匠心追求,保障了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的高标准和专业性。
四、多维发展:群策群力深耕项目资源
在高效率、高质量完成国家项目的同时,“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编辑也群策群力,在基础史料中深耕细作。通过挖掘项目本身的作者资源,项目团队开拓出一系列优秀图书选题,为读者奉献出一系列凝结中国学界智力结晶的原创学术精品。如系统策划出版了“西北民族文献与文化研究丛书”,该丛书由西北民族大学才让教授主编,共分10册。其中收入才让教授三部专著《藏传佛教信仰与民俗(增订本)》《藏传佛教文献与文化交流》《菩提遗珠:法藏敦煌文献的整理与解读》,董晓荣的《察哈尔格西传记研究》,杨富学的《回鹘佛教文献研究》,多洛肯的《明清甘宁青进士征录》,扎西当知的《敦煌古藏文占卜文书整理翻译研究》及张秀清的《〈祖堂集〉与敦煌文献校读》。
依托专业的文献整理出版经验,编辑在民族文献出版方面进一步深挖选题潜力,深度开发选题价值,形成选题梯队,出版产品结构进一步延伸,出版内容更加丰富,品牌整合功效显著。“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资金资助项目《格萨尔文库》是其中的一大亮点。《格萨尔》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之瑰宝,被国际学术界誉为“东方的荷马史诗”。《格萨尔文库》是多民族、多语种、多版本《格萨尔》的整理翻译集成。该文库发掘整理了藏族《格萨尔》早期珍藏版本,并进行了科学梳理和划分;增加了藏、蒙古等多民族异本资料,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格萨(斯)尔》;忠实记录了土族、裕固族《格萨尔》的珍贵史料。总之,文库兼顾了藏族、蒙古族、土族、裕固族《格萨尔》史诗,并全部加以汉译,搜集并厘清了一百多种早期版本,版本齐全程度及善本数量远超目前出版的《格萨尔》,又具有严格的辨伪标准,填补了土族、裕固族《格萨尔》文本整理的空白。《格萨尔文库》的出版,开启并极大促进了《格萨尔》史诗的“经典化”。此外,与中央民族大学合作的“古代维吾尔语诗歌集成”、与中国人民大学合作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欧亚古典学研究丛书”等精品学术丛书甫一出版即备受好评,这些选题在所涉语种、民族研究方面也进一步丰富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民族文献出版格局,使上海古籍出版社成为我国民族文献出版的重要阵地。
互联网时代,随着数字化技术的纵深发展,出版社在立足高品质学术图书出版的同时,也积极探索历史史料融合出版的模式。我们初步计划在写本文献全部刊布后,建立包括敦煌古藏文文献在内的“敦煌吐鲁番集成出版数据库”,通过数字化手段较完整地保存这批珍贵的文献、文物资料,建成一个融学术性、权威性、适用性、安全性于一体的文献数据库,依托数据库平台强大的功能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服务。
自2004年“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运作以来,一代代藏学专家、出版人肩负历史使命,薪火相传,为这项具有重大原创性的精品文化工程殚精竭虑,孜孜不倦。我国出版业进入了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新一代上海古籍出版人定当以“敦煌古藏文文献出版工程”的运作为契机,将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古籍宝库中的璀璨明珠——敦煌西域古藏文文献,整理好、出版好,为汉藏文化交流的历史与民族团结的未来作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法藏敦煌藏文文献(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2]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英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献(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3]甘肃省文物局,敦煌研究院.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1)[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4]束锡红.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史料价值和出版意义[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8(3):120-122.
[5]黄维忠.古藏文文献在线项目及其《法国国立图书馆和大英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文献》[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2(4):78-79,95.
[6]束锡红.《法藏敦煌藏文文献》发布会暨敦煌藏学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J].中国藏学,2008(1):239-241.
[7]万玛项杰.《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敦煌研究院卷)出版[J].敦煌研究,2018(1):79.
[8]陈鹏鸣.学者型编辑更要发扬工匠精神[J].出版参考,2016(12):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