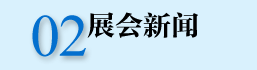【作 者】孙玮、李梦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摘 要】出版作为一种社会知识生产和公开化的实践,关乎人类文明的发展。随着数字技术的崛起,由印刷术和线性文字所定义的现代出版业正遭遇巨变,出版与社会的关系面临重构。数字技术重塑了出版的形态和方式,实现了不同文本类型的动态拼贴,融合了渗透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多重知识生产网络,开启了人类社会知识生产、传播的新模式。
【关键词】数字出版;知识公开化;超文本;交互性
引言
出版作为一个现代概念,是由四个关键词锚定其基本意义的:文字、印刷、知识、公开。在它作为一种社会事业诞生时,非常集中地指向一种媒介——书刊。痴迷书籍的作家博尔赫斯说,人类使用的工具都是人体的延伸,“显微镜、望远镜是眼睛的延伸;电话是嗓音的延伸;我们又有犁和剑,它们是手臂的延伸”。他当然不是在复述麦克卢汉,这些铺垫只为突出一点,“最令人惊叹的无疑是书籍。——书籍是另一回事:书籍是记忆和想象的延伸”[1]。在此,媒介被截然分为两类,拓展具象的身体感官,延伸抽象的情感意识。在博尔赫斯看来,书籍和其他工具的不同,在于实现了人类内在性的外显化。考虑到不依赖文字、没有印刷术之前公开表达的人类实践早已存在——苏格拉底、孔子、释迦摩尼等人类早期思想家的口语交流已经树立了典范,书籍出版的最关键点,恐怕就是文字印刷与口语对话作为不同媒介方式的特殊意义了。关于印刷术以及相关议题的研究可说是汗牛充栋,诸如认知方式的迁移、社会关系的变革等方面都有多维度的展开,它与宗教改革、民主政治、文化产业之显著关联,更构成了社会发展史的标志性事件。现代印刷出版业称得上是人类文明历史中的一座高峰,毫无疑问地,这个行业的产生直接受惠于媒介技术的变革。
依照博尔赫斯的媒介分类法,印刷出版业之所以创造了人类文明的丰功伟绩,依赖于它的媒介特质——舍弃口语交流的感官元素。“有学者认为,90%的口头交流仍然是非语言交流,说话的方式比说话的内容更重要。然而,当口语转写为书面语之后,口语的残余部分即非语言的声音、手势和语体被抽取走了,书面交流成为纯观念的交流,其基础是书面词语的意义。”[2]书刊依托于印刷技术,将抽象观念的传播从特定时空语境中抽离,人类延伸“记忆和想象”的方式越来越趋向于脱离身体和具体时空。现代印刷出版业将文字的这个特性推向一个新阶段,属于少数人的书写文字转变为大众化的印刷品。人类知识公开化的过程发生了重大变化,引发了社会各个领域的变革。印刷出版业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与口头交流甚至书写传播的区别很大,它展现了一个公共与私人交织的复杂过程,传播与接受分离成两个场景。在传播方面,它夷平了层层套嵌、多重叠加的人际关系网络,实现了超越人际网络、脱离具体时空的大规模点对面的传播,这也与手抄书阶段的社会层级性传播形成鲜明对比;在接受一端,它将口语对话公开化的活动转变为私人默读书刊的方式,斩断了阅读作为一种身体性的、在地化的社会交往方式的历史。现代出版业的这些传播特征宣示了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模拟电子技术的出现使得出版业突破了文字印刷的边界,音像出版成为一种新型方式,但这个声音、影像因素的呈现并非口语时代即时对话式交流的还原。模拟技术复制了诸如听觉、视觉的感官元素,但它并不构成一个特定时空中即时互动的身体性社会交往,而是呈现了全球化脱域进程中的虚拟在场的传播。
立足于数字技术的崛起,当前的出版业早已无法用原初的关键词来概括了。呈现方式已经不局限于文字、印刷,知识的边界日益模糊,甚至连“公开”也疑点重重,因为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情形下,其达成的重点已经从“能够发声”渐渐转变为“可以被听到”,这正是媒介技术演变所引发的出版业巨变。如果我们把“人类的记忆和想象的延伸”——博尔赫斯的文学话语或可改写为社会性地生产与传播知识——作为出版的稳定性内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出版关乎人类文明之大事),那么在数字技术进入最新的媒介形态序列之时,如何理解出版业的变革就成为当前我们考察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视点。
一、超文本:纸是敌人
数字出版最易为大众感知的端倪是其对印刷文本的突破。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一批小说家开始尝试超文本小说,其中最为经典的是乔伊斯的《下午,一则故事》和莫斯洛普的《胜利花园》,两者都以计算机磁盘的形式发行,强调文本的开放性,将超链接插入文内,读者可以点击链接进入不同的情节,每个人可能看到完全不同的故事。[3]iPad电子书设计中的经典——T.S.艾略特的《荒原》,展示了电子书的超文本特征,它融合了艾略特的手稿以及包括艾略特本人在内的诗人、名人、演员朗诵诗歌的录音版本。[4]“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以超文本思路建立了一个线上开放电子图书馆,“为中外学者提供中国历代传世文献,力图超越印刷媒体限制,通过电子科技探索新方式与古代文献进行沟通。收藏的文本已超过三万部著作,并有五十亿字之多,故为历代中文文献资料库最大者”[5]。其超文本的特点体现为,采取维基百科的操作方式,使用者可以共同编辑原典文献内容,协助对照不同的影印版进行勘误。这项主要由研究机构承担的专业工作,现在开放给更多普通个人。[6]超文本实践在全球出版业形成一股强劲风潮,人们渐渐地意识到,数字出版并非将纸质文本原封不动地放置到数字媒介上,它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知识生产和传输的方式。1965年,泰德·尼尔森在论文《一种复杂、可变、不固定的文本结构》中,极具开创性地提出了“超文本”的概念,意指“非序列性的(non-sequential)写作——文本相互交叉并允许读者自由选择”[7]。他强调超文本的结构不是线性的,而是“一系列通过链接而联系在一起的文本块(text chunks)”,这些“各自独立又相互链接的文本片段”,可以有无限多可能的阅读顺序。[8]所以“对尼尔森来说,纸是敌人”[9]——“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对纸张所隐含的监禁感到愤怒……这是思想不应该承受的限制”[10]。于是他总是斜挎一根长长的肩带,上面夹满了笔、剪刀、便签纸、胶带、订书机[11],“这些是他连接事物的工具,也是他对抗纸质世界的弹药”[12]。他认为,“纸张的问题是,每个句子都想突围,向其他方向滑动,但页面的限制却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所以,如果页面能够长出翅膀,或是在一侧长出隧道,那么插入的文字就可以一直写下去,而不会在某一点之后停止”,“被困在纸上的我笨拙地模拟了这种(超文本的)平行性”。[13]何为“超文本”?尼尔森解释说:“它指以一种复杂的方式相互连接的书面或图像材料,无法方便地在纸上呈现或表示。它可能包含摘要或内容,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映射;它可能包含研究它的学者的注释、补充和脚注。这样的系统可以无限发展,逐渐包括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书面知识。”[14]“传统文本有固定的顺序: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或相反)、一页接一页,它是顺序的、线性的。信息却不一定是这样。无数的作者,无穷的文字,数不尽的评论、解释、参考和引用塑造了信息之间复杂的关系。传统文本在呈现复杂关系上有太多不便。与传统文本不同,超文本用超链接再现信息之间的联系,它是非顺序、非线性的。”[15]也因此,考斯基马认为,“超文本的一个最大优势便是它再现信息的‘真实’结构的能力。此外,当信息十分复杂之时,超文本将是再现它的唯一可能方式”[16]。
超文本展现了数字出版的精髓:非线性逻辑生产、展现和传播知识的形式。这种形式才是数字技术的关键所在,它突出的是文本的关联性意义,文本的价值只有在关系网络中才能显现。这个想法并非自数字技术始,克里斯蒂娃改造自巴赫金文本对话性理论的“互文性”概念,强调了文本是作为文本网络的一个部分而获得意义的。[17]但正如延森所指出的,“大部分互文性的研究并未对读者或受众给予经验性关注”[18]。延森认为,菲斯克纵横两个方向的互文性观点将大众的交流纳入文本,具有开拓性。横向的互文性指文本意义跨越历史的迁移;纵向的互文性则侧重于在较短时间内传播主题、事件和议程的媒介系统,正是在纵向互文性中,受众被吸纳进来,受众围绕文本的交流包括反馈和相互对话,构成了第三级文本。[19]菲斯克的三级双向文本论,将文本概念从编码者拓展至解码者,受众的解码构成了新一轮编码,突破了原作者对于编码的垄断,互文性的文本网络自静态话语文本拓展到了人之动态的话语互动。但菲斯克的受众文本论,非常明显是基于模拟技术媒介的,虽然超越了印刷文本线性逻辑、静态话语文本的限制,但仍然局限于媒介分割、互动延迟,或只能称得上的是多层级文本。只有数字技术才使得“互文性成为一系列明确的、可操作的结构——超文本性(hypertextuality)”[20]。
超文本的出现预示着从印刷技术到数字技术的迭代,出版业的变革开启了人类社会知识生产、展示、传播的新模式。所谓纸是敌人,意味着纸张代表的信息方式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知识发展的态势;或者反过来讲,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社会公开发行知识的方式得以重塑,这可以看作当前出版议题的一体两面。纸是敌人的姿态,正是对印刷技术与信息特质之间内在张力的强烈感知。超文本超越的不仅仅是印刷纸的文本,它还打破了人类文明存在已久的多重区隔。当前移动数字技术在延森援引菲斯克探讨超链接的基础上实现了进一步的超越,从抽象化符号的信息文本延伸到了实体具象的空间,这是数字技术的颠覆性突破,虚实空间之间的屏障被击穿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数字技术与以电视为代表的模拟技术之间出现了断裂。比如恐怖片历史上里程碑式的电影《午夜凶铃》有一个经典情节,贞子爬出了电视机。这个情节之所以异常惊悚,是因为大大地出人意料。在模拟技术时代,电视机里的场景不过是信息编织的虚拟空间,只能作用于人的意识,并不能即时并具身地延伸到实体空间,所以这个场景可说是创作者的极致想象。直到数字技术崛起,文本才出现了虚实交融的可能。“普适计算融合不同的自然物体、人工产品和社会环境中的多种媒介界面,进而实现了‘世界作为一个媒介’的构想。”印刷文本作为出版的一个主要界面,正在渐渐转变为“有机用户界面”[21],这种界面不但与使用者如影随形,而且可以随时随地实现虚拟与现实的转换。如此,不但身体、行动都被纳入文本中,而且可以实现不同文本类型的动态化拼贴,文本呈现出永不停歇动态拼贴的状态,以服务于不同主体的目标。超文本创造的复合空间,叠加非线性的复线时间,造就了史无前例的新型文本,在世间的一切都可以数据化的技术语境中,所有的存在物都将被纳入文本。如此,和正在剧烈转型的其他大众媒介类似,出版业也正在遭遇巨大挑战,因为它诞生时依赖的核心技术(印刷术)及其创造出的文本(线性文本),正在失去原初的形态。纸作为敌人被打倒之后,现代出版业将何去何从?
二、交互性:弥散性机遇
被誉为法国文学史登峰之作的《忏悔录》的首次公开亮相,并非出版业所为。由于法国王室禁止其出版,1768年冬季卢梭被迫从书中选出若干章节,在巴黎的一系列集会上朗读,据说当时上流社会的支持者们感动得泪流满面。在1781年至1788年间,这部巨著终于得以出版发行,当时卢梭已辞世。[22]这个出版史上的经典个案体现了出版业对社会知识公开化的巨大影响。印刷术应用于现代出版业,一方面使得知识得以大规模突破社会层级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出版业对于知识公开的垄断。在《忏悔录》这个个案中,出版业的中心化结构性力量与口语传播的弥散性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出版业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数字出版的超文本性改变了这个局面,它使得口语交流和印刷品传播出现了大规模融合的可能,这有赖于数字技术的交互性。
众多的新媒体研究者认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断裂,集中体现于其独特的“交互性”。“新媒体的交互性与各种双向传播或者被动传播不同,而传统的大众传媒则主要依靠后者来激励观众参与(例如信件和民意调查)。自其伊始,新媒体的交互性就是即时的,并且‘实时’地发挥功效。”从理论上而言,它还包含民主的潜能:“相较于单向传播,真正意义上的交互传播具有下述正式属性——要求参与者更加平等,沟通权力更加对等。”[23]数字技术的交互性改变了印刷出版业的基本状态,被印刷出版业切割得七零八落的古典对话式交流出现了融合的可能——公开发行中的传播和接受重新回到同一个时空。出版业专业化构成的社会垄断也正在不断被打破。数字出版的交互性引发了出版史上的一个大转折,交互以各种维度渐次展开,包括文本的交互、出版机构与读者的交互、编码与解码的交互、人与物的交互、多维度时空交互、社会关系网络交互、权力交互等。盖恩等概括了交互性概念涉及的四种路径:从技术角度看待交互性,认为交互潜能根植于不同媒介系统的软硬件之中;从人类能动性角度界定交互性,将人类参与和设计或使用的自由度看作界定的变量;新媒体用户之间的交流,孕育了人际沟通的新的可能;视交互性为一种政治概念,认为它与政府治理与公民身份的广泛变迁密不可分。[24]以这四重交互性概念考察数字出版,可以概括当前出版业一个显著的趋向:出版的弥散性。如果局限于现有专业出版机构的视野,这种弥散性或可被视为行业的巨大危机,现代出版业正在经历被瓦解的过程。但假设将观察尺度放大,这种弥散性状态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知识生产迈向一个新阶段,由此释放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能量。
弥散性与当前出版业讨论的诸多议题有关,比如生产主体的多元化、内容的分散性、形式的多样性、接受的分享性等,但弥散性不同于这些概念的一点,是其立足于自人类社会有文明以来知识生产及公开化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基于数字技术的渗透性,这种公开化的知识生产与日常生活产生的关系。因此,弥散性意指当前的知识生产呈现出一种与日常生活紧密勾连、互相渗透的状态,这不但与古典时期特定人群和时空的对话式交流不同,也与中心化出版业的专业化区分开来。数字出版的弥散性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主体的弥散性。这包括了出版主体多元化的含义,但不仅于此。主体多元化旨在描绘越来越多的社会企业加入了出版业,以及出版专业机构的内容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参与生产,这还是局限在专业平台用户生产的层面,没有凸显数字媒介的知识生产已经突破专业平台的界域,弥漫渗透在大众的日常生活中。比如网络文学类、科普类的知识生产,小红书、微信群自组织专业教育等,都是在专业出版机构之外开辟了知识生产及公开化的全新场域,分享及阐释社群的动态性非专业生产成为一种常态。“新的读者创造新的文本,新的意义是文本的新形式发挥作用的结果。”“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嘴里说的,甚至数数本身,都是文本。”[25]其二,形式与内容的弥散性。这个议题不仅涉及专业出版机构的市场化细分,而且关乎对于知识边界的定义权及其游戏规则的重新确定。自有文字以来,知识生产及其规约都以精英化作为主要趋势。现代出版业产生之后,知识垄断在接受一端受到极大冲击,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有机会通过出版物接触各类知识;但在生产一端,出版业高度专业性的门槛阻止了大众广泛参与知识生产过程。数字技术在生产方极大地拓展了知识内容的边界,专业知识的生产边界不断模糊、重构,[26]呈现为一种变动不居的状况;在生产、展现和传播形式上,出版专业工作也与日常生活互相渗透。由此,整个社会对于知识的界定及其公开化的机制与规则也在急速变化中。其三,社会网络及权力的弥散性。出版系统集中体现了知识社会关系网络的基本状态及其蕴含的权力运作机制。每一种媒介形态的知识生产,都编织了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口语对话时代的知识生产及公开化具有古典民主的特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弱势群体(如奴隶、女性等)有排斥性,但其传播仍保持了相当大的开放度,普通大众有广泛参与的可能,这也孕育了人类文明早期的民主雏形,如雅典城邦的直接民主。[27]书写文明的社会关系网络逐渐趋向于区隔状态,知识生产为识文断字的精英阶层独占,目不识丁的普通大众无缘涉足。现代出版业的社会关系网络分裂成两个极端——生产的高度专业垄断与接受的大规模普及。出版机构的专业化门槛为现代民主的法律制度所确认,出版发行成为社会知识生产的专门化系统,以此确立了自身在知识生产中的权力中心地位。数字出版正在创造渗透在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多重知识生产网络,由此不断挑战、消解现代出版业构筑的专业化、中心化知识社会网络。
数字出版呈现的弥散性趋向,一时间被视为出版业的危机,因为它触动了现代出版业的根基——基于印刷技术的知识生产的行业性垄断。但换一个视角看,数字技术提供给出版业的机遇更加彻底。所谓彻底,是指数字技术的融合性特质把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知识公开化形态一网打尽,它展现了知识生产形态的无限可能性。数字技术既可以呈现单一形态的方式,也可以任意组合历时性的不同形态从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形态。以人类早期的知识生产为例,口语交流曾经是精英惯用且局部地普惠大众的主要形态,现代出版业则几乎摧毁了这种形态。本雅明这样描绘这个历史性的转折:“我们最保险的所有,从我们身上给剥夺了:这就是交流经验的能力。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很明显:经验已经贬值。经验看似仍在持续下跌,无有尽期。只消浏览一下报纸就表明经验已跌至新的低谷。一夜之间,不仅我们对外在世界,而且精神世界的图景都经历了原先不可思议的巨变。一种现象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越发显著,至今未有停顿之势……十年之后潮涌般的描写战争的书籍中倾泻的内容,绝不是口口相传的经验,这毫不足怪……身体经验沦为机械性的冲突,道德经验为当权者操纵。”[28]本雅明将报纸、书籍等现代出版业指认为剥夺人类口语交流直接经验的罪魁。数字出版却神奇般地“复原”了这一切。近年来风靡一时的社交媒体Clubhouse,展示了与古典的面对面对话式交流以及虚拟现身永远在线的新媒体传播既相关又截然不同的新型状态。它采用即时性音频对话的形式,参与者根据自行选择的主题,进入形形色色的群体(“房间”)进行交流,主题五花八门,形式也灵活多样,有事先约定的主题和主讲者,也有任意随性的即时发言。[29]Clubhouse一反网络虚拟空间的通行规则,整个过程杜绝录音,强调即时和暂时性的真实在场。使用者认为,与基于文字、图像的平台相比,音频的真实性和亲切感使得人们相互交流的动态产生了更加诚实的对话。[30]“感觉更像是咖啡馆或酒吧。”[31]有时像晚宴一样,有影响力的名人讨论当天的紧迫问题,但大多数时候是普通专业人士在找联络的机会。迪米洛尔斯女士说:“即时性与让事情发挥作用之间达成了一种很酷的平衡。”[32]出版业对于音频的利用正在出现一个热潮,比如著名电商亚马逊的有声读物服务Audible正在全球范围内扩展,Amazon Echo和Google Home等智能扬声器使用户能够按需收听音乐、播客或最新天气报告。Clubhouse这样的社交媒体或可称为“声音广场”,它将前现代、现代、当下的出版形态融合在一起,展现了数字出版未来发展的新可能。
三、结语
数字技术对出版业的冲击,是自出版成为一种专业化机构以来最彻底的一次,类似于新闻媒体正在经历的整体转型,大众传播所依赖的复制模拟技术已经为数字智能技术所取代,印刷术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互构机制遭遇挑战,这个前提是当前讨论数字出版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因此,出版和社会之关系的重构,构成了当前考察数字出版的重要视角,数字技术给出版业带来的危机不能视为对出版价值的怀疑,正如新闻专业机构面临的挑战并不意味着新闻价值的丧失。相反,出版、新闻的意义在新媒体时代必将得到进一步拓展和彰显。关键问题在于,新闻出版业如何在数字技术环境下,找到并建立自身与人类文明的新型连接方式。达成这一目标的必要前提是充分理解数字技术的特质及其在出版领域所引发的变革,所谓超文本、交互性,都正体现了数字出版的技术性特点,这预示着出版必将突破既有格局,在这个历史性进程中,出版的价值也将获得新一轮重构。
现代出版业作为人类社会的一项伟大事业,创造了数不胜数的奇迹,它对人类文明的价值无论怎样评估也不为过。但事情的另一面是,这些耀眼光环也使得人们很自然地倾向于将出版的意义固化在现代出版业这种专业机构形态上,这个思维惯性亟待反思。当前出版业作为社会专门化机构正在全方位迎接行业转型,整个行业处于重塑的进程中。因此,除了专业机构本身的转型思考,跳出行业视角,以更宏阔的尺度考察数字出版的未来发展,将出版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是思考出版在数字时代意义与价值的一种新思路。长久以来,出版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公开化实践,其社会意义的开掘比较多地落实于现代出版业对政治、经济、文化、个人等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当这种具有中心化的行业形态渐渐地被数字技术局部消解时,出版的价值将落在何处而得以继续彰显呢?此时,回顾历史或可获得别样的启发:在现代出版业产生之前,人类知识生产的公开化实践是如何展开的?正如在专业的新闻媒介产生之前人类就有大量的新闻实践一样,具有出版意义的实践也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尽管那时候并没有汇聚成出版这个词汇。追溯人类文明初始阶段,所谓知识生产的公开化,就是苏格拉底式的当众演讲。在古希腊人的生活中,言说对于人的价值更多地落实在这个行动本身。阿伦特援引亚里士多德对于人的第二个著名定义,是“能言说的存在”[33],由此阐释了公共领域的涵义。在这个思路中,公开化是人之存在以及构成实在的基础。“显现——不仅被他人看到而且被我们自己看到和听到——构成着实在……生就是在人们中间。”[34]这种公开化的实践构成了“公共”,它意味着,“任何在公共场合出现的东西能被所有人看到和听到,有最大程度的公开性”[35]。这种构成人类存在的公共言说的知识生产形态,随着媒介变迁渐渐地转化为书写文字(比如柏拉图以文字记录的方式使得苏格拉底哲学流传后世)、印刷出版业、音像出版乃至数字出版,出版的意义也随着其形态的演变不断转化、拓展,但公开化实践对于人之存在及公共领域的价值,不仅不应当从出版的内涵中被剔除,相反或许正构成了数字出版的核心价值,超文本、交互性等正显示了数字出版在公开化实践方面的巨大动能。
这预示着出版(知识的公开化)必将突破既有的格局。事实上,当前大众的数字媒介实践已经显现了出版多元化发展的态势,这种创新实践比比皆是,比如网络文学的持续性爆发式增长显示出非专业出版的巨大能量和前景;又如,基于数字技术在中国城市场景中大规模发生的公共阅读实现了从私人默读到公共朗读、从文本阅读到身体实践的两个转变,这种城市公共文化实践,可视为一种崭新的出版形态。[36]这提示我们,数字出版的变革无法也不能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理解,它必然与出版的社会价值与文化意义形成关联。当前,印刷出版业奠定的人类知识生产的基本模式正在发生各个向度的转变,数字出版的可能性发展方向层出不穷。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当专业化知识生产的主导模式被渐渐地、局部地消解时,当下这种弥散性的、去中心化的知识生产如何与社会形成新型勾连?专业与业余的出版实践如何互动互构以创造数字时代的出版新形态?这不仅仅是专业出版机构而是整个社会面临的问题。当前或可预见的是,出版业的专业性不再仅限于行业垄断机构,知识、公开化、出版等概念的含义急剧改变,出版与大众及公共性的关系更加紧密;等等。概言之,数字技术颠覆性地冲击着现代出版业的过程,正是出版的核心价值及其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不断拓展的历史进程。
注释
[1]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口述[M].黄志良,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1.
[2]洛根.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M].何道宽,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9.
[3]蔡春露.《胜利花园》:一座赛博迷宫[J].当代外国文学,2010,31(3):97-105.
[4]SADOKIERSKI Z.Master craftsman: How TS eliot led the way in the digital publishing revolution[EB/OL].(2013-11-05)[2021-05-04].https://theconversation.com/master-craftsman-how-ts-eliot-led-the-way-in-the-digital-publishing-revolution-19689.
[5]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本站介绍[EB/OL].[2021-05-04].https://ctext.org/zhs.
[6]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维基区[EB/OL].[2021-05-04].https://ctext.org/wiki.pl?if=gb.
[7][8][16]考斯基马.数字文学:从文本到超文本及其超越[M].单小曦,陈后亮,聂春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37,38,61.
[9][12][13][14][15]李恪.超文本和超链接[M].北京:新星出版社,2021:91,91,91,90,90.
[10]NELSON H T.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and xanadu[J].ACM Computing Surveys,1999,31(4):37.
[11]BARNET B.The magical place of literary memory:xanadu[J].Screening the Past,2005(18).
[17][18][19][20][21]延森.媒介融合:网络传播、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三重维度[M].刘君,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94,94,95,96,86-87.
[22]费希尔.阅读的历史[M].李瑞林,贺莺,杨晓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45.
[23][24]盖恩,比尔.新媒介:关键概念[M].刘君,周竞男,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90,92.
[25]戴联斌.从书籍史到阅读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78.
[26]施宏俊.六个词重新定义出版业[EB/OL].(2017-09-15)[2021-05-06].https://www.bookdao.com/article/401226.
[27]库蕾.古希腊的交流[M].邓丽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8]本雅明.讲故事的人[M]//阿伦特.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95-96.
[29][31][32]VIGNA P.Inside the clubhouse: What's all the fuss about silicon valley's exclusive social media App?[N].The Wall Street Journal,2020-07-15.
[30]RADCLIFFE D.Audio chatrooms like clubhouse have become the hot new media by tapping into the age-old appeal of the human voice[EB/OL].(2021-02-26)[2021-05-06].https://theconversation.com/audio-chatrooms-like-clubhouse-have-become-the-hot-new-media-by-tapping-into-the-age-old-appeal-of-the-human-voice-155444.
[33][34][35]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17,32-33,32.
[36]孙玮,褚传弘.移动阅读:新媒体时代的城市公共文化实践[J].探索与争鸣,2019(3):118-126+144.